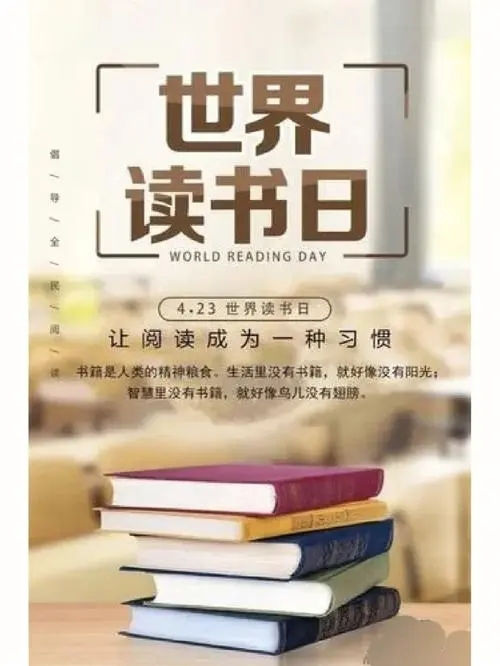1816年,英国从埃尔金伯爵手上收购了来自雅典的巴底农神庙大理石浮雕,并将其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这批堪称古希腊艺术的典范之作震惊了当时整个欧洲的文化艺术界,人们认为这些雕塑将“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欧洲艺术”。最近,看到一本新出版的《牛津西方艺术史》,第一张插图就是陈列这批巴底农石雕的大英博物馆杜维恩厅,展厅天花板和地角的四条延伸线将观者的视线聚集于后墙前的《命运三女神》,她们和这个厅中的其他杰作一起成为了筑起欧洲艺术的基石。
从第一部分“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到最后一部分“现代主义及其后”,在图片的引领下,我们仿佛穿过一条西方艺术的长廊。遥想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该有多少艺术巨制存留于世,岂是几本艺术史所能涵盖的?翻开一本艺术史书也许出于偶然,而创造、了解并享受艺术是否是人生的必然呢?
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言:“鸠集遗失,鉴玩整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画,毕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敝衣, 减粮食。妻子童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这句话后来演变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如果从功利主义者的角度理解,是会得出“妻子童仆”般的结论:艺术确实不当吃、不当喝,只是一些“无益”之事。但如果从唤醒欧洲艺术的巴底农神庙石雕甚至更久远的古埃及狮身人面像一路向东,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伊什塔尔门、古印度的桑奇药叉直至中国的各种伟大遗迹,纵观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伟业,又有多少不是这些“无益”之事的成果呢?人生有涯,如果艺术当真“无益”,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投身其中,为之孜孜不倦?
米开朗基罗在创作完他晚期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墓碑《晨》、《暮》、《昼》、《夜》后,用诗句明示了那些岩石里包裹的秘密:“睡眠是甜蜜的,成为顽石更幸福;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不见不闻,无知无觉,于我是最大的快乐;不要惊醒我啊!”米开朗基罗毕生都在工作,他一切亲力亲为,忙起来时,和衣而睡,仅以几片面包果腹。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在用岩石“创造”生命,而是在“解放”生命。他26岁时就“解放”了《哀悼基督》的圣母,30岁时“解放”了《大卫》。他甚至用了四年的漫长时间,独自创造了西斯廷礼拜堂天顶上的一个璀璨的艺术世界。
这些天才般的艺术作品就像一些具有吸纳和保管功能的魔石,艺术家把自己的激情与生命贯注其中,通过它们传递千年,并投射到每个现代的欣赏者身上。凝视这些作品,我们常常会震慑,因为我们在感受来自遥远年代的智慧,这是大自然和自己生命的一种联系,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鲜的信息,它根源于人的本心。你以为你听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声音吗?不,那是你自己心底的声音——伟大的艺术能唤醒人们麻木的神经,回归到原初的本真状态。在那里,人性与自然没有隔阂,融为一体。一呼吸间,天地鸿蒙;一刹那时,宇宙洪荒。就像第一次从水中看见自己的倒影,第一次从别处听到自己的呼吸,谁能不为此心跳加速、血脉贲张?
这也许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如果我们用逻辑的方式思考一下艺术的价值,相信也不会得出完全悖谬的结论。关于艺术的功能与作用,艺术学基础理论著作已经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说,虽然各家各派的总结不尽相同,但归而言之,都离不开情感诉求或精神表达的需要。孔子在齐闻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苏珊·朗格也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可见,艺术不仅可以满足人的情感与精神需要,有时这种精神需要甚至比物质需求更加强烈。
就当下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理性精神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这种机械文明与人类自然属性的严重脱节也造就了现代人比过往更甚的焦虑与紧张。在古斯塔夫·卡耶博特的《雨天的巴黎》中,在乔治·修拉的《在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中,街道、建筑、草坪、湖水、绅士和淑女,画中每个元素都那么中规中矩,这些集合了巴黎的时尚与繁荣的风景却永恒地记载了人们在现代城市浮华外表下内心的疏离。于是,19世纪末,高更放弃了看似衣食无忧的证券交易所工作移居塔西提,希望在那里发现未经污染的世界;凡·高也曾试图逃脱,移居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也许最后他们失望了,高更用画面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凡·高用旋转的《星空》和预言性的柏树表达心中问题永远多于答案后郁结而成的焦虑……
我们应该去感谢那些所谓神经质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痛苦转化成艺术创作的激情,精血凝练,浇铸成心。有了他们,我们才能不必靠寻求另类刺激提醒自己身体的存在,不必让自己的心灵像笼中困兽那样去左突右撞。艺术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浅言之,是情感之慰藉,深言之,是人性之关怀。当海子把自己的生命交付铁轨的时候,人们却长久念诵着他的“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当疲惫的灵魂从艺术中寻找到飞翔的翅膀时,它才能拍手作歌。(作者:王凯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