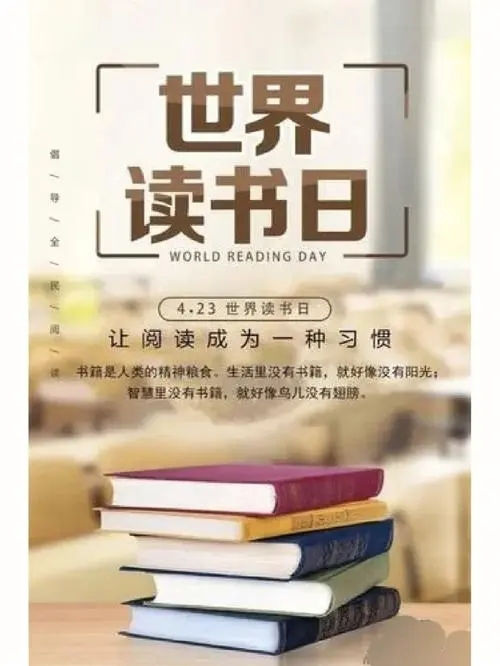我总觉得文学理想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不需要谈论。一旦我们需要谈论它时,就意味着它已出现了问题。
远的不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总体上是不存在理想问题的。那个年代虽然有对历史创伤记忆的书写,也有种种迷惘、感伤、苦闷与困惑的文学话语,但作家的写作都很真诚,文学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一种向上的精神气质。1981年,汪曾祺写出《大淖记事》后说:“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我去看‘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40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祺反复提到他写的是“向往”,而在我看来,这种向往其实就是文学理想。
实际上,这种向往也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王蒙的《春之声》,张承志的《黑骏马》与《北方的河》,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铁凝的《哦,香雪》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把作家自己的理想转化成了某种文学理想,文学也因为理想之光的烛照,一下子有了精气神。
于是有必要追问,为什么文学理想在80年代不成其为问题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以为与那个年代的总体氛围关系密切。李陀说:“80年代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激情,觉得既然自己已经‘解放’了,那就有必要回头看自己经历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往前看,看历史又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马上做什么。”(《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53页)这种说法很有道理。80年代的过来人回想一下,李陀所谓的激情其实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之类的歌曲唱的是激情,《一个和八个》《红高粱》之类的电影演的是激情,而“美学热”、“全民读书热”、“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等,也无不与激情有关。1988年5月,我曾参加在芜湖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亲眼目睹了分组讨论时那种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的辩论场面。显然,那也是一种激情的体现。如此激情燃烧,让80年代变得生机勃勃,理想主义的疯长也有了合适的土壤。
文学理想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勃兰兑斯曾经谈论过1830年代对于法国文学的重要性——类似于文艺复兴似的时代精神状况,作家亲同手足般的思想交流与艺术批评,共同催生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参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第8-18页)198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状况也颇有点法国当年的味道。西风东渐、思想解放、创作自由、人道主义、启蒙精神等等,让作家们唤发出前所未有的写作热情。这个时候,写作活动不光是文学理想的呈现,同时也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某种预演。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作为五四文学的继承者,80年代的文学最大限度地接通了鲁迅所描述的文学理想,也把文学理想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90年代的来临,文学理想或被搁置或被抛弃,文学开始“向下”滑行——与80年代文学形而上的精神气质相比,90年代的文学更多关注柴米油盐、饮食男女之类的日常琐事。1991年韩少功说:“前不久我翻阅几本小说杂志,吃惊地发现某些技术能手实在活得无聊,如果挤干他们作品中聪明的水分,如果伸出指头查地图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的几句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它们无论怎样怪诞怎样蛮荒怎样随意性怎样散装英语,差不多绝大多数作品的内容(——我很不时髦地使用‘内容’这个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因为偷情,所以大倡人性解放;因为乏味,所以怨天尤人满面悲容。这当然是文学颇为重要的当代主题之一。但历经了极左专制又历经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国民们,在精神的大劫难大熔冶之后,最高水准的精神倘若只是一部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书,这种文坛实在太没能耐。”(《灵魂的声音》)当偷情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时,我们当然不能说这就是文学的理想或理想的文学。而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也业已证明,文学逃避灵魂问题去处往往就是肉欲之乡。在这种书写中,作家的灵魂麻痹了,读者的要求降低了,文学的理想也暗淡了。
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局面依然与时代的精神状况有关。90年代以来,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等等盛行,却惟独没有了理想主义生长的地盘。而那些众多的主义不光是对理想主义形成了一种挤压,也对它构成了一种消解。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器”成为一个时代的重点琢磨对象时,它当然不可能在“道”的层面上有所作为。同时,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引领下,人们也开始远离“道”,嘲讽“道”,形而上的追求仿佛成了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1993年,关于“躲避崇高”的争论和对“伪崇高”的批判,置于当年的历史语境并结合有的论者的中庸思想分析,或许这种批判本身并无多大问题。但今天看来,“躲避崇高”这种提法显然也是对流行时代趣味的一种呼应与确认——当时代开始了“下行”的历程后,作家没有显出超越之姿,而是委婉地强调着和光同尘的合法性。
被这样一种时代氛围笼罩,文学已不可能有太大出息。在这里,我当然不是说90年代以来的文学就一无是处,而是说没有了文学理想之光的照耀,文学已显得真气涣散。于是,文学要不描写的是《一地鸡毛》似的无奈人生,要不体现的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苟活哲学,还有《废都》那样的颓废相,《上海宝贝》那样的暴露癖,再加上“私人化写作”的盛行,“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的泛滥,文学陷入到媚俗(kitsch)叙事中而不能自拔。李建军说:“从精神上看,我们时代的文学的确存在着一股邪气。在某些作家看来,文学本来就是变态的、畸形的,而作家天生就是一群‘莽汉’,一群在道德上享有放纵特权的‘糙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一些作家把自己的兴趣,牢固地锁定在描写性欲、金钱、权力和暴力方面。不是说这些内容不能写,而是他们的叙事态度是病态的,流露出的格调和趣味是低下的。(《文学主于正气说》)李建军思考的问题是今日文学正气不足邪气有余,他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触及到了理想主义退场之后文学的委靡之相。
文学的委靡之相当然是时代精神状况的产物,而这种精神状况首先作用的却是作家,这就不得不涉及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在我看来,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虽然说起来复杂,但有两种关系更值得注意:其一是顺应,其二是反抗。当时代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象时,顺应时代便能让作家身心舒展,文学也会呈现出刚健之风、进取之态,盛唐时代的诗歌便可作如是观。而当时代变得物欲横流或委靡不振时,顺应便成为一种共谋,文学因此也会遭殃,这时候就有了反抗。反抗是作家的自我拯救,同时也是让文学振作起来的一种手段,但势单力薄的反抗往往又会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举动。当然,顺应与反抗也并非那么纯粹,许多时候它们都相互纠缠,从而让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暧昧。比如歌德已是一位伟大作家,但恩格斯却依然分析出了他与时代关系的矛盾性:“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这里特意提到了德国的鄙俗气,那应该就是当年德国的时代精神状况。连歌德都被这种时代精神击中而无还手之力,可见其鄙俗气的强大。
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中其实也是存在着一股鄙俗之气的,但许多作家或者浑然不觉,或者予以认同。如此一来,文学自然也就浊气上升,清气下降,失去了清俊挺拔之姿。这其中自然也有反抗的作家,但他们的言行却一度受到批判和嘲讽。遥想90年代中期的张承志和张炜,他们曾有过“抵抗投降”的激烈言辞,今天看来,或许二张就是抵抗鄙俗之气的先知先觉者。然而,不但他们被扣上一顶“道德理想主义”的帽子而遭到攻击,就是“抵抗投降”的先驱鲁迅先生也受到了牵连。在这种质疑、嘲讽与批判中,反抗时代的流行趣味不但成为尴尬之举,而且似乎也成了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正是由于诸多作家与时代鄙俗之气明里暗里的合谋,理想主义换算成道德理想主义后被清剿出局,文坛或文学从此进入到你好我好他也好的太平时代。
海德格尔说,贫乏的时代往往会隐藏存在和遮蔽存在,诗人的职责在于认识时代的贫乏,进而让存在敞开。(《诗·语言·思》,第85页)这当然是对作家的高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很可能还难以企及。那么,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可以向恩格斯所批判的歌德学习,退而求其次?如此这般之后,作家在顺应与反抗时代之间游走,进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这时候,他们的作品或许才能呈现出灵魂的悸动,心灵的歌哭,而不至于成为一种无病呻吟的平面化的东西。
然而,学习歌德也颇不容易,因为歌德是非常看重文学理想的。他认为,欧里庇得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艺趣味是前进而不是倒退的”(《歌德谈话录》,第86页)。他指出,近代文学界之所以弊病多多,原因在于“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同上,第92页)他呼吁:“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同上,第137页)这里所谓的前进的文艺趣味,作家高尚的人格,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都可看做歌德对文学理想的向往与追寻。我们的作家也能形成类似歌德这样的感受与思考吗?我不清楚,但还是希望他们多少能有 一点,因为这是让我们的文学有大出息的基本前提。(赵勇)
- 上一篇: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 下一篇: 新闻出版总署:支持新闻出版企业上市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