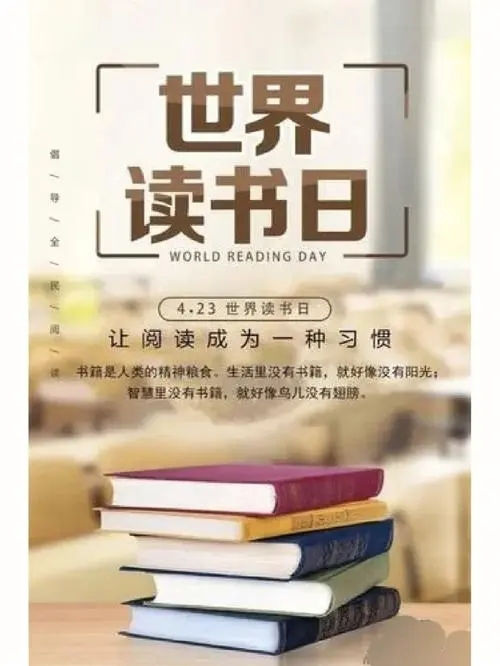岁月似乎没有在梁晓声的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诸如成熟,诸如世故……他依然那么秉直善良,真诚倔犟。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做一个像胡适、蔡元培那样的,中国的、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
“当年蔡先生都是步行去北大,人家送他马车都不要,更别说汽车了。出入校门见了工友还会鞠躬,且是发自内心的谦卑。”梁晓声一直坚信不移的是,文化应该担负起培养公民品行、抚慰和温暖他们倍感伤痛的心灵的职责。
近些年来,相比此前的诸多作品,梁晓声似乎给读者的印象淡了。
他写于199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近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先前,他认为时评类的书另有评价的标准,需要冷静、客观、公允、详实的依据。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情绪色彩太浓。但是时代变了,当他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当年看到的那样。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的书也应该要变化。现在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抢救’,希望通过修改尽量使之‘重见天日’。”再版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新增了《关于土地的杂感》、《关于青年和新中国的杂感》等多篇重量级文章。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在十几年后再版,梁晓声也觉得,知青群体是特别值得独辟一节来讲行评说的,但再版时仍然没能补遗。梁晓声是如何考虑的? “我不太愿意使这本书,因为增加太多内容变得跟当年相比面目全非。在修改的时候,也没准备好这方面的材料。所有阶层,包括农民和当年相比,生存状态都有所 改观。本书呈现当时的状况,会使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谁变化得最多最快,我们应该通过比较要加以重视。”
梁晓声最近在为即将出版的知青日记写序,他发现,知青们当年的日记内容,关键词是忠诚、革命、献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判……唯独缺少年轻 人应有的细致感情。比如有知青负责给队里敲钟,他会写敲的是革命的钟,战争的钟,阶级斗争的警钟,似乎要敲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他们写的日记是发自真心 的,今天看来却很荒诞。但“上山下乡”客观上却使当年的广大中国城市青年与中国的农民尤其是最穷苦的农民紧密地同时也是亲密地结合了十年之久。这使他们对 于“中国”二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使他们对于“人民”二字具有了感情化的了解。
类似《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样的“非小说”,在梁晓声的创作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少。在他1600万字左右的作品中,散文时评的文字占了三分之 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批评。“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我的另一支笔一直是这样写过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不是突然出现的。中外 有相当一批作家们也是这样的,我在下乡之前就读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和柏拉图文集,不但读小说,还读他们的时评。我理解的作家就应该是这样的, 不能只摆平了书桌写小说。”
梁晓声最近连续写了两个电视剧,都是关于知青题材的。他说,最初接到和知青有关的题材时,他本能的反应是排斥的,常常想不应该再写了。“可是接 下来我会想,这个题材在今天写还有什么值得的。如果给我空间,允许我表达,我会写下去,因为在文化生活中看不到对那个年代的表现了。我不但是在写返城人 物,也是在重新呈现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的端点是什么样子呢?它决定了现在的状态。我们支持改革开放,在那时充满理想主义,我们可能要的是玫瑰;现在得到玫 瑰,可是玫瑰有花也有刺,而且不是一般的刺——这跟当年的理想期望值是有差异的。 接下来我还会写有关思考国家、民族命题的文章,这些都是文学。”梁晓声说,他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于面对稿纸只写小说的人,也不认为只有那样定位了才能写出不 朽的作品。鲁迅不是也写了大量的杂文吗?我不但是作家,还是文化知识分子,还要肩负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在创作了大量的知青题材的小说之后,梁晓声的目光转向平民生活,他觉得自己的平民立场“相当顽固”。“中国老百姓身上虽然有很多负面的、传统的、消极的文化背景存在,但是也有很多好的方面——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另外,中国老百姓之间还是有一种善的关系存在的。”
现代文化的变异和现实社会的压力,常常使梁晓声感到忧虑。有一次,在书店的讲座上,他坦率地说:“正直、同情、无私、社会公益心、助人为乐,经常处于被践踏、被嘲笑、被解构的境地。”容忍这样的一种文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受到惩罚。
梁晓声曾在很多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从《龙年1988》、《九三断想》到《凝视九七》,从1988年到1997年的10年时间,梁晓声不断 提出将来谁还愿意当农民的问题。到1997年,不吐不快的感觉推动他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前期作品明显有投枪和匕首的味道。然而上世纪 90年代后期至今,梁晓声的写作风格开始有些转变。在长篇小说《恐惧》、《泯灭》之后,他描写现代都市的《伊人,伊人》,进一步显示了风格转变。到了今年 新出版的《上蹿下跳的人们》,开头几篇都是谈民主。他说:“知识分子要担当国家的民主责任,不只是科技救国,不只是繁荣经济,不只是社会稳定,不只是丰富 文化生活,不只是提供娱乐,还要担当起知识分子的民主责任。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炒明星、炒故事、炒学术丑闻的兴趣超过了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前景、民主模式 的关注?超过了思考整个国家构建社会公正、呼唤良知?《上蹿下跳的人们》没有故事,没有搞笑,没有可以作为谈资的腐败,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我要做的。由此 我也会常常感到孤独。”但是他毫不犹豫无所畏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他坚信自己是看得准的。
“我要求自己在作品中不要一味批判,也要给予,变成蝙蝠和蜜蜂。蝙蝠本身有着警示的象征,蜜蜂却要酿蜜,这两者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作为作家,这两方面的文艺功能都要争取实践一下,而且要实践得好一些。”
梁晓声说,自己从少年时期就热爱文学,从兵团创作员一路走过来,文学变成他此生唯一每天都在尽心的事情。回顾以前,至少有两点总结:“凡是我的 哪部作品好一点,都由于我在创作中没考虑到市场、稿费、印数、改编成影视收入多少,我只是相对真诚地把我的感受呈现出来;凡是我的作品中我个人觉得不好 的、失败的,都是由于后一些因素进入了我的创作意识。有时候某些因素会产生诱惑。”他说,自己现在毕竟没有必要靠写作赚钱,也不用在编剧中考虑哪个元素受 到观众欢迎来借此提高收视率。一路写来,写作者所剩时间不多,要把自己摆放在文学、文艺、文化和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作为写作者, 必须考虑怎样写才能更对得起写了这么长时间的作者的身份。
来源:工人日报
- 上一篇: 中国人读书“四病”
- 下一篇:中国出版社死拼版税外国作家狮子大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