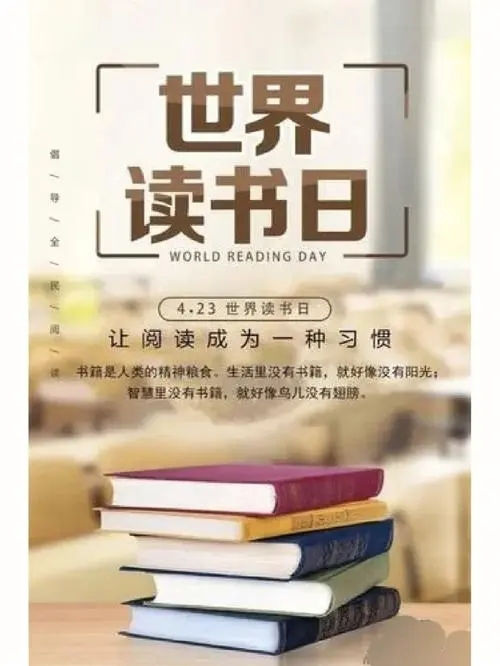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布雷勒斯的墙和新疆胡杨
时间:2018-06-19作者:中国先锋作家出版社
阅读:次
每当先辈文学家逝世之际,总有报纸和杂志来让我说点什么。年轻的时候,我总是逐一答应着谈点或写点什么,虽然认为那些不过是一些浅薄的、感伤的东西,但对于自身确实被内心哀悼之情驱使而说和写这一点,我并不怀疑。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有些对不起那些特地赶来求我讲点什么的人了,嘴渐渐沉重得不想张开,笔也变得很涩,这样的经验不断地重复着。怎么说呢,只能单纯这样理解吧: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自己,同时,相应地生也以重复的形式直接迫近了……
接到井上靖先生的死讯的夜里,我只是默默地听着音乐。直到深夜,电话铃声还接连响个不停,那期间我随意地接了其中一个电话,说了自己心中被寂寞荒凉裹挟形成了旋涡似的空白的话。也没反问一句是哪家报纸,就折回到工作室的床上。去井上先生家守灵时,一位只见过面的年长的名人用带刺的话对我说,你那谈话是不是欠点和追悼相应的礼节。回家以后,我把几家报纸找来,自己说的话一--实际上报纸的记载是符合事实的一一我也是初次读到它。
内容如下,“井上先生不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小说家,也不是一个感觉锐利的诗人。可是,他一旦展开故事,其小说、诗便都呈现出独特的魅力。井上先生是当代非常有名的人物,因而,对他的批评生前也有。然而,在日本文学的法文翻译事业上,他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我和他一起去过中国和法国,作为旅行者的井上先生最令人怀念。”
责备我的人们,可能觉得我这里没说悲痛的话是难以原谅的吧。那么他们注意的仍然是单纯的事情,在很久以前,对于人的死我一直怀着不绝的悲痛,并且,并不把悲痛之词挂在嘴上。然而,内心里涌现的近似荒凉的悲哀,远比年轻时沉重和剧烈……
即使对于井上先生的死,我对不识一面的新闻记者也没有能说出悲痛之词。于是,那应该说是根本的妥当的,是我在守灵时从远处看到的井上夫人那只能称作漂亮的姿态,和仿佛被巨大的一击而抑制不住内心悲伤的中国来的吊唁客人的举止。那几乎可以说是生涯无二的悲哀。我并不是由于大脑欠损,勿宁说由于经验重叠而陷入了失语症状态,有时觉得自己作为小说家,莫不是真的要无所事事地度过晚年了吗……
令人怀念一词,对于如此的我来说更为珍贵。准确地说,比起和他在一起,我在托井上先生的福参加的那几次旅行中能够感到难得的轻松愉快。先生自身就是罕见的旅行者。同时,他又具有让同行的人都感到自由解放的特殊能力。
在布雷勒斯的街角,我们在寺院的厢房躲避急雨时,广场对面的建筑物墙壁上显现出美丽的颜色。井上先生的感叹和表情,唤起了周围的人自然深切的同感。----这很像我昨天买的皮包的颜色,他说。回到了旅馆我们一看他说的皮包,竟是完全不同的颜色。那与滑稽可笑缠绕在一起的令人怀念的情景。
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我们坐车在砾漠上旅行。逐渐开阔的谷底流淌着清澄的溪水,还有那萌发出红、白、黑色苞芽的各种胡杨。这时,我注意到井上先生,他眺望着对面那似乎展现了绝对孤独的一无所有的砾漠……那令人怀念的威严与和谐的神情。
我多次被井上先生的地位和影响力所庇护,然而,对其耀眼的光辉却坦率地折服了。也就是说,我将来也和如此的光辉无缘,但如能在井上先生诗集中追寻到和那种令人怀念的东西相贯通的血脉就够了。远离井上先生熟识的辉煌而有力的世界,我想对于已经不再是现世人的井上先生的怀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醇化吧。
- 上一篇:芥川龙之介:女体
- 下一篇:《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 将亮相国庆荧屏

作家动态